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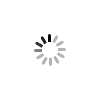
▲蔡泽荣,山神漆器创始人,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、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。
大概手艺人都是务实的,与人吃饭喝酒谈情怀,都不及守在工作室钻研作品。大概手艺人都是专注的,一旦入行就一条路走到底,不惜拒绝路上更多更好的风景。大概手艺人都是谦和的,不管站在多高的位置,只愿低头关心粮食和蔬菜,待人接物充满真诚与热情。蔡泽荣就是这样的典型,前半生,他把山神漆器从一个小厂房做成了一个产业园,而现在,他想守住一座山,让重庆漆器在这里结出生生不息的果实。这个愿景,或许要穷尽一生去灌溉,不过他甘之如饴,无所顾忌。
“漆匠是一门高尚的职业。”
蔡泽荣生长在重庆最北边的一个县城,名叫城口。这里是大巴山的腹地,依山傍水,冬暖夏凉。城口这个地方过去交通闭塞,与外界基本隔绝,是一个自给自足的“桃花源”。正因为如此,城口的手工艺反而得到了良好的生长土壤。早些年,这里与工业品无缘,物资运不进来,所有的日用品,包括劳动工具都是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制造出来的。比如耕地的犁头、簸箕、墨纸、竹席、板凳、桌子甚至房子。这里手工艺种类丰富,石匠、木匠、砖匠、瓦匠、漆匠这些手艺人在当时是一种高尚的职业。
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,城口被称为“中国生漆之乡”。在十岁左右,蔡泽荣就开始跟漆树打交道。小时候家里清贫,他上山砍柴时,身体大面积接触到漆树,结果皮肤过敏,又红又痒了好些天。到了1969年,蔡泽荣初中刚毕业,人民公社安排他下乡,14岁的他体重只有三十多公斤,生产队见他太瘦小,不愿收他。为了谋生存,父母只好把他送到一个漆匠那里跟师学艺,所谓跟师学艺就是师父只管三餐,其他生活开销都不管。他没有钱理发,没有钱补衣服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失去上学机会,蔡泽荣便安心跟着师父学艺。
当时规定徒弟要三年才能出师。“教一路,留一路,防止徒弟打师父。”师父留了一手,没有教给蔡泽荣核心的技术,只让他磨砂,刮灰,打下手。这样刮三年灰,磨三年砂,修修补补又三年,就是九年的光阴。蔡泽荣意识到这样下去学不到熬漆的手艺,这是制漆最关键的一步,需要把天然生漆的水分脱掉,但在脱水过程中,温度稍微高一点,整个漆器就报废了。如何把握这个度,师父只字不提,每次熬漆总是背着他。于是不到两年的时间,他就离开师父,后来在姑父邓万春的指点下,学会了熬制桐油和生漆。从那以后,蔡泽荣便成了当地的漆匠,活跃在大山里。
1993年,蔡泽荣租了一个小厂房,起名为飞亚漆器厂。一开始是为了向日本出口漆碗而建的。没想到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,蔡泽荣发现国内市场的需求比日本更大,于是他把市场转向了国内,并改名为“山神”。“这个厂建在大山里面,山给它提供了基地,我们制漆用的材料,从实木到生漆全都取之于大巴山。祖国的山河有无数的宝藏,各种文化资源取之不尽,大山的灵气也给了我们创作的灵感,所以我想我们的名字一定离不开山。再者,漆器是中华民族的瑰宝,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,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得有神韵,‘山神’的名字由此而来。而当这个名字诞生的时候,就决定了我们所用的材料必须取决于大山,漆器一定要做到极致,品质要求和发展方向,要对得起大山的馈赠,这也是我们企业的文化。”在蔡泽荣的精雕细琢之下,城口的漆艺,成为了一种当之无愧的高尚。
“传承传统文化需要手艺人的挑剔与坚持。”
生漆也叫大漆、土漆,它是从漆树的树皮层割下来的一种树脂。蔡泽荣介绍说,在海拔800~1200米的地方,一般产的漆是小木漆,这种漆表面看起来很好看,但它在结成漆膜之后,它的韧性,以及经久、耐磨及不褪色的程度,相比大木漆就差多了。大木漆多数生长在海拔1500米以上,比起小木漆,大木漆的产量低得多。城口的生漆绝大多数是大木漆,所以这里的生漆比周边的市场价格都贵,1千克大概260元。“但漆中一般有35%左右的水分,还有残渣,如果将水和残渣过滤掉,这1千克里只有50%的漆。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是用传统的火来脱掉漆的水分,涉及到电费、材料和人工费,算起来精制后的生漆1千克要在800元左右。而化学漆1千克在20元左右,不管是漆的成本,还是施工的难度,比起生漆要廉价得多。”
漆器制品的成本很高,但往往消费者对漆器缺乏认知,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,一味追求低价。这对于中国漆器的发展非常不利。蔡泽荣眉头紧锁,表达了他的忧虑:“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漆器的价格,低于成本太多,一看就是假货。”入行50年,蔡泽荣一眼就能辨别出哪些漆器是生漆,哪些是腰果漆。腰果漆主要产自于广东福建等地,属于树脂型的油基漆,使用简便、价格低廉,含有苯酚和甲醛等有害物质。比起生漆,腰果漆不过敏,在艺术院校教学时,使用腰果漆更为合适,但老师要有正确的引导。当然在创作时还是要使用大漆,那才叫真正的漆器。
山神漆器晶莹剔透,质地精细,色彩和图案极具考究,其工艺复杂程度是其他手工制品难以比拟的。“漆器的制作周期非常长。我举个例子,一件漆器上的每一遍漆要干燥7天,如果掌握的气候、湿度不够合适,要10天以上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。并且漆器制品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也多,如冰裂、刮痕、气泡、起皱,特别是小颗粒,凸起来的是颗粒,凹进去的是毛孔,而要解决这些问题,就需要在工艺上精益求精。”
对“精”的要求,蔡泽荣从第一步选材就开始了。木质要细腻,纤维韧性要好,木胎要脱脂。裱布要使用夏布,刮灰使用的配漆也得是生漆。漆灰的颜色像瓦罐一样,得让它呈现出质感,这就需要“植皮”,然后是各式髹饰工艺的综合运用,堆漆、变涂、螺钿、犀皮等,再是一遍遍地上漆,直到达到他满意的效果。博采众家之长,尤其追求色泽的丰富与透亮,最后形成了山神漆器的独特风格。
2005年6月,蔡泽荣接到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的参评通知后,加班加点制作了3件作品,脱胎花瓶、镶嵌漆盘和另一件实木花瓶,经面试、答辩,顺利通过评审。蔡泽荣清楚地记得,经信委和评审组给他的评语是:蔡泽荣对中国漆艺的研究、对重庆漆器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简短有力的一句话,让他坚定了要把这门手艺做下去的信念。而颁奖时,时任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亲临现场,为他颁发证书。当时黄市长讲了这样几句话:“我非常羡慕手工艺者,非常羡慕你们这一届所评上的工艺美术大师。因为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你们,祝贺你们。”政府的评语和市场的鼓励,成为日后蔡泽荣推进山神漆器发展的强心剂。
过去没有提工匠精神,专注于做一件事情,是父辈教导蔡泽荣的。“现在想来很有道理,干一件事情就要一条路走到底。更别说这是传统工艺、传统文化。几千年的更迭都没有消失的东西,就需要我们把它传承和发扬下去。”蔡泽荣在城口办漆器厂的时候,有很多机会进入建筑、锰矿、钡矿、煤矿等高收益的行业,但是他没有改变最初的选择。“既然入行做了漆工,那深耕漆艺文化就是我一辈子的事业,自己选择的路,坚持走到底就对了。”
“一切都在自然生长,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”
传统工艺都是创新而来的,我们的祖先一开始也没有这些技艺,每一个年代、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手工艺,都是随着创新而发展的。山神漆器一开始是在城口传统漆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,每年都有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,哪怕是生漆的材料,在它精制的过程中也能用一些创新的手段,使其在保留原来的韧性、防腐性的同时,让干燥速度快一点、透明度好一点、色彩丰富一点。如果几个月都没有新的思路,技术也停留在原地,蔡泽荣就会有深深的危机感。今年习主席讲了一段话,“中国制造要立于世界不败之地,创新是灵魂,质量是生命,人才是根本。”他认为非常受用,只要抓住了创新、抓住了质量、抓住了人才,手工艺也好,制造业也好,一定能持续、稳定地发展。
20多年来,蔡泽荣积极参加各种展会,在他看来,参展是传统工艺美术企业一个非常有效的推动市场销售的方式。从深圳、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青岛,到北边的大连、伊春,西部的太原、鄂尔多斯、兰州,都有蔡泽荣和山神漆器的印记。在参展的过程中,通过与不同地方的人接触、交流,蔡泽荣了解到各地的风俗以及对工艺美术的欣赏和要求的差异,又反促他进行产品创新与升级。至今,蔡泽荣还坚持每年参加10余个展会。
但传统工艺美术企业的市场,现在的确遇到了大的瓶颈。十多年前,大部分手工艺行业是政府批量采购。“从某种角度讲,这推动了传统工艺的发展,激励了一大批手工业者参与到手工行业中来。”但近两年政府采购叫停,蔡泽荣的精力也从过去应付政府采购,转向了对市场的研究、对产品的研发。“最近两年,我们新产品推出的速度比过去快了。也就是说我们能应付市场的需求,即便在过渡时期,我们也能高高兴兴、踏踏实实地做研发和创新,加强我们软实力的培育。”
在蔡泽荣的身上,有多重身份:大师、企业家、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城口漆艺代表传承人以及重庆工美行业协会会长。大师需要精湛的技术,企业家需要独到的经营能力,传承人需要带好徒弟,作为工艺美术行业会长,更需要思考、服务和带动一个城市工艺美术的发展、人才的培养以及文化的传承。所以蔡泽荣一直特别忙碌,但60多岁的人,却依旧保持着青春的活力,因为他有太多事情要做。“我就恨自己时间太少,不然还可以研发出更多精品。”
20余载里,山神漆器从一个小厂房,已成长为重庆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知名品牌,目前正在准备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未来还将打造成为集文化展览、研发制作、手作体验、产品销售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中国漆文化产业园。
尽管手工艺行业不好做,但在蔡泽荣心中没有“困难”两字,他说一切都在自然生长,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闲谈间,蔡泽荣透露出他深埋于心的愿景:“我想在对面的大山里找一块地,种上一大片的漆树,再建一个手艺人的交流地,和对外的漆艺原生态体验馆,让城口的漆文化,渗透到更远的地方去。”
说这句话的时候,蔡泽荣带着微醺的表情,让这个愿景听起来,有一种近在眼前的真实。如他所说,一切自会水到渠成。